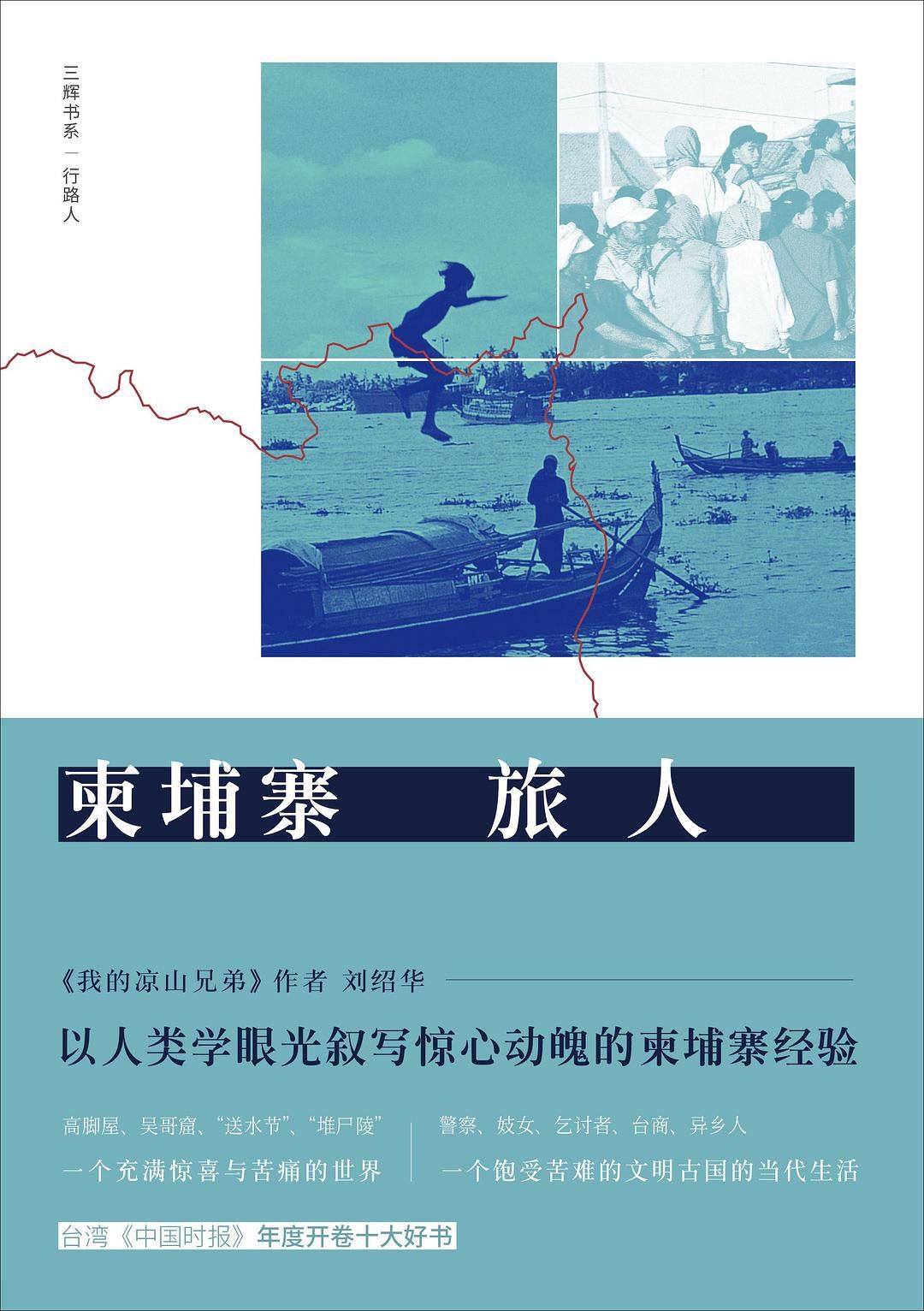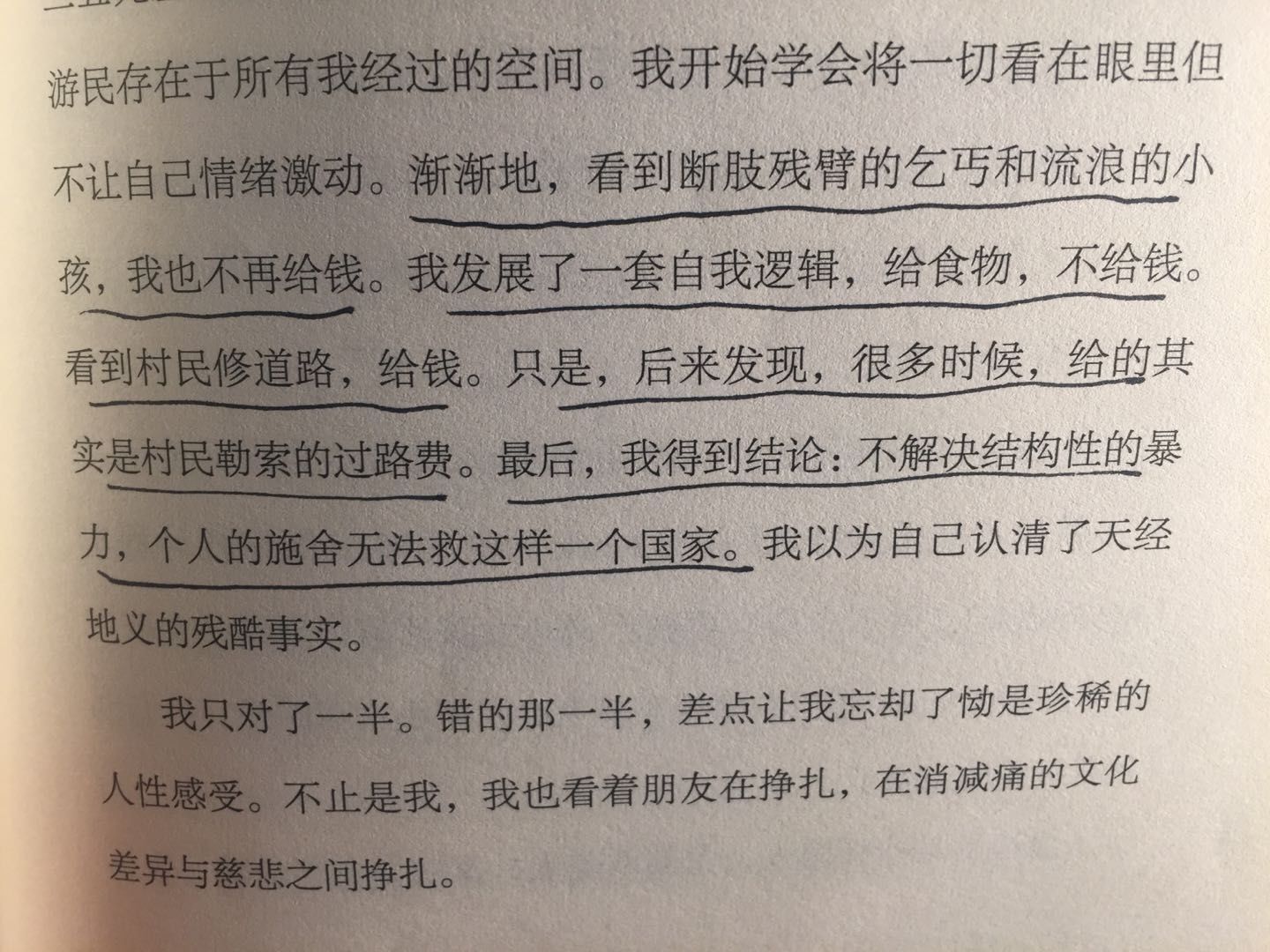“小翻书党”为澎湃新闻·翻书党栏目最新推出的子栏目,意在分享编辑的私人阅读体验。只要是诚意之作,不应简单用“好”、“坏”来评判,因此我们并不着意推荐,只希望读者在不经意间邂逅自己想读的书。最近,一个能用九国语言卖纪念品的柬埔寨男孩火了。一名游客在柬埔寨吴哥窟录下和这个小男孩的对话,五分钟的视频里切换了中文、法语、日语、英语、泰语、西班牙语、马来语、菲律宾语等语言,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。人们在赞叹男孩语言天赋的同时,也关注到柬埔寨儿童的成长环境。据报道,这名柬埔寨男孩称自己每天上午上学,下午在景点售卖纪念品,他的弟弟也是售卖纪念品大军中的一员。视频中,男孩用中文对拍摄者说:“买一个啦,买一个我唱歌给你听。”然后他真的唱起了来,还是改编的国内“神曲”:“我们不一样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,我们在这里,卖东西给你……”柬埔寨孩子的成长环境与20年前相比有进步吗?多语种交流,除了是特殊技能,是否还源于复杂历史留下的文化烙印?
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柬埔寨男孩,右为视频拍摄者Venus,系马来西亚华人(一)二十年前,台湾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也曾和卖东西的柬埔寨小孩相遇。1998年,刘绍华加入非营利组织“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”,在柬埔寨生活了两年。她在湄公河的渡船上遇到过一个卖口香糖的小女孩。那是雨季,十一二岁的瘦弱小女孩在大雨滂沱中敲打她的车窗。她直觉的反应是,有人卖东西,不要理会。可是小女孩固执地举着手中的青箭口香糖,眼睛在豆粒大的雨中挣扎着努力张开,隔着车窗看着她,她终于于心不忍,摇下车窗递给小女孩一张湿透的千元柬币。小女孩的手上套着透明塑料袋,里面抓着廉价的口香糖,自己被淋得不能更透了,却仍维护着手里的东西。她感到了深深的苦涩。“当她慢慢地把口香糖隔着塑胶袋递给我时,我已分不清我脸上的泪水和雨水。”刘绍华后来回忆道。多年以后,刘绍华以人类学家的视角把柬埔寨经历写成书,题为《柬埔寨旅人》。她写了许多柬埔寨的孩子。河边的擦鞋童,死心塌地地重复问她“要不要擦鞋”;放牛的孩子,视若无睹地进入有地雷标志的警戒区;“寡妇岛”上的小朋友,带她去看被屠杀者的森森白骨,在阳光下笑得灿烂无比。苦难和漠然令她印象深刻。“他们不是不知苦痛,只是在这样有如此悲惨过去与艰苦现状的国家,他们对悲痛恐惧的感受和我不同。”她写道。
《柬埔寨旅人》,刘绍华著,三辉图书/中央编译出版社,2017年刘绍华后来以《我的凉山兄弟:毒品、艾滋与流动青年》
(群学,2013)一书成名,她说,那项研究也受惠于柬埔寨经验的花果。二十年过去,今昔情况不尽相同,当时的柬埔寨有更多悲苦。她见识了普遍的赤贫,看见了众多被地雷炸伤的身障者,知道了许多艾滋患者生活在周遭,拜访过以茅草竹片为墙的监狱。刚到柬埔寨时,“几乎天天在捐钱”。老小乞丐、被地雷炸掉一条腿的年轻人、病人、游民……无处不在。渐渐地,耐痛度越来越高,甚至练就了漠然的本事。
第31页但她自省:只对了一半。“错的那一半,差点让我忘却了恸是珍稀的人性感受。”一番挣扎之后,她决定不应放弃人性中最基本的同情。“我但愿自己和他一样被骗,而不是被自以为是的理性囚禁。”她意识到,“恸”是一种文化差异,而“我没能克服痛的文化差异,悲恸始终存在”。
《柬埔寨旅人》并非游记,而是民族志。刘绍华以人类学的眼光,写出了外来者的观察,也写出了对“外来者”自身的反思。她描绘了柬埔寨形形色色的外国人。有五花八门的国际组织,有来做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,有自以为是、高高在上的白人男性,也有认真坚韧的西方女性友人,有不同国籍的东南亚妓女,有“包二奶”的台商,有淘金梦灭的中国姑娘,有黑帮大佬,还有回乡赚钱但对故乡处境无比漠然的海外柬埔寨人。“柬埔寨是个光怪陆离的国家。除了近二十年内乱的历史因素外,成为西方国家的民主实验地也是造成它怪异的原因。”刘绍华写道。以金边为例,这里“拥有贫穷国家难得的硬件建设,也存在发达国家无法理解的紊乱落后”。她观察到,光是她在柬埔寨的两年内,金边就有一两百个国际NGO注册进驻,没有注册的组织也号称有一两百个,展开教育、健康、地雷、游民等各项发展协助计划。而国际组织大量进驻带来了各种问题,比如打乱原有的货币制度和市场经济:
上一篇:6岁前学外语和不学外语的孩子有什么差别?这份
下一篇:没有了